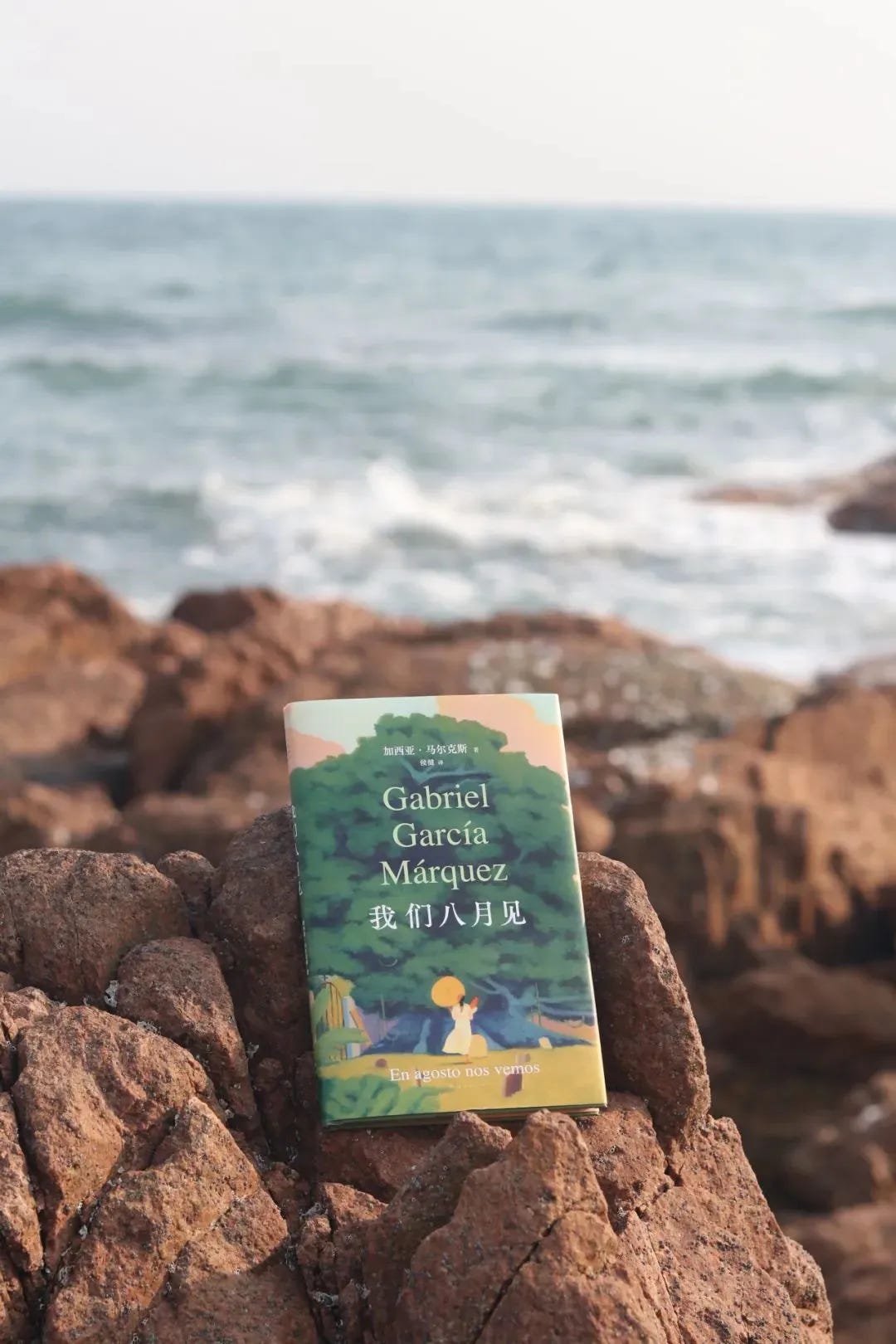在《我们八月见》的开头,马尔克斯为读者勾勒出了这样一位主人公的形象:女主角安娜·马格达莱纳·巴赫和丈夫拥有令旁人艳羡的生活,结婚二十七年依旧关系融洽,还育有已长大成人的一对儿女。然而,平淡的生活下,隐藏着安娜·马格达莱纳未曾被满足过的、对于浪漫和自由的向往。看似幸福美满的婚姻将她束缚在了一个没有生命力的虚伪形象中。小说后面写道,打开母亲的棺木时,她“在棺中看到了自己,笑容僵硬,双臂交叉放在胸前”。这个不自然的自我防御姿势,正是她在婚姻中个人状态的写照。
当安娜·马格达莱纳又一年登上小岛,为死前执意要葬在岛上的母亲扫墓时,她平淡的生活却出现了一条裂缝:她和一个素昧谋面的陌生人发生了一场激情四射的艳遇。被压抑许久的生命力带着希冀和热情倾泻而出,从此后每年八月登岛给母亲扫墓时,她都会期待着艳遇的发生。
在小说中,她质疑自己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太过可悲:“为了一晚上的偶遇耗费剩余的人生等待一整年,这种做法太荒唐了。”作为读者的我,却完全可以理解这份荒唐。只有在小岛上,远离了婚姻生活的规范,安娜·马格达莱纳才能充分地绽放自己的美;而只有那些在她生活中昙花一现的男人,才能够完全欣赏她真正的个人魅力。
在小说的最后,安娜·马格达莱纳无意间发现,其实母亲在岛上也曾有一位情人。她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母亲生前每年都会以做生意为由上岛三、四次,也明白了为什么母亲死后执意要被葬在岛上。这一刻,母亲和女儿两代人的命运形成了镜像,安娜·马格达莱纳发现,原来母亲和她有着同样的压抑和放纵、剥夺与渴求。她意识到,“自己生命中出现的奇迹实际上是母亲生命的一种延续。”这种世代之间不可避免的命运轮回,是马尔克斯最喜爱的主题之一,在《百年孤独》中就是串联起全书脉络的线索,而在这部更加小巧的作品中则通过女儿为母亲扫墓的片段展现。
小说的结尾令人意犹未尽。安娜·马格达莱纳派人将母亲从墓中掘出,背着母亲的尸骨袋,永久地道别了小岛,回到了自己家。面对惊愕的丈夫,她说:
“母亲什么都明白。其实我觉得,她是唯一的明白人,当她决定让大家把她葬在那座岛上时,就早已明白了一切。”
母亲明白的是什么呢?安娜·马格达莱纳又为什么要把母亲的尸骨带走呢?我想,母亲明白的是,只有岛上才承载着她真正的生命。她坚持将自己葬在岛上,是因为她只在岛上真正地活过。而安娜·马格达莱纳在母亲的棺中看到了一面镜子,里面是她在重复母亲的命运。她意识到,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每年岛上短短几天的时光终究是荒唐的。那些时光看似美妙,但实则”飘渺“。她之所以将象征着母女俩命运的尸骨带回家中,是因为她不甘只做母亲的镜像,而是要在自己全部的生活中重拾真正的自我。
于是,她“最后一次满含同情地回望了一眼自己的过去,永远告别了属于那些夜晚的陌生男人,也告别了被她散落在岛上的无数飘渺的时光。”安娜·马格达莱纳从岛上带走的,不只是母亲的尸骨,也是她自己的。